
中国典籍“谁来译”
[摘要]在讲述中国故事、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时代当下,我们应当客观、公正地看待中国典籍翻译实践和接受之间的窘况与差距,从中国的典籍翻译大家身上汲取翻译的智慧,获取前行的力量和指导。

杨宪益(右)、戴乃迭夫妇青年时期合影。
中华文化“走出去”,在更广阔的话语系统中构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已经成为急迫的时代命题。然而,典籍外译与接受历史,以及近年来中国文化“走出去”所遇到的障碍,再次凸显了翻译过程中“谁来译”的问题。
对于中国译者承担典籍翻译的问题,大多数西方学者持否定态度。英国汉学家葛瑞汉说:“……在翻译上我们几乎不能放手给中国人,因为按照一般规律,翻译都是从外语译成母语,而不是从母语译成外语的,这一规律很少例外。”美国当代著名汉学家、《中国文学选集》编译者宇文所安也表达了类似观点:“中国正在花钱把中文典籍翻译成英语。但这项工作绝不可能奏效。没有人会读这些英文译本。中国可以更明智地使用其资源。不管我的中文有多棒,我都绝不可能把英文作品翻译成满意的中文。译者始终都应该把外语翻译成自己的母语,绝不该把母语翻译成外语。”他们之所以言之凿凿,大多因为秉持“翻译一般只能译入母语而不是译成外语”的信条,认为中国译者的翻译造成了难以忍受的“中国英语”,相较之下,西方译者则行文流畅、自然、可读性高。姑且撇开此一论点的武断之处不论,检视典籍外译批评领域诸如话语建构和文本形象建构等关键性问题,也可以发现此类论断脱离原文谈论译文的片面性和不恰当性。
由于中国学者进入典籍英译领域时间相对较晚,据现有汉学书目统计,中国典籍译本绝大多数是由西方汉学家或独立、或在中国合作者帮助下承担完成的。但统计数字只能说明过去的客观存在,并不足以作为中国学者不能担任典籍翻译主体的理论证据。传教士以降的西方译者为中国典籍的异域传扬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由于受到“本族文化中心主义”影响,以往的西方译者翻译中国文化典籍时,大多采取迎合译语读者的归化翻译策略,翻译过程中曲解、误译中国文化之处比比皆是。此外,承载古代经典文本的汉语语言具有语义的浑圆性、语法的意合性和修辞的空灵性这三大特点,构成了文本结构在各个语义层面的似隐还显,充满理解张力,具有极高的抗译性,使得绝大多数外国学习者难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触碰中华文化内核。然而,典籍英译的主要目的,是向西方世界介绍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和发展,让西方了解真正的中国。译者努力使中国典籍易于被西方读者接受,并不意味着应当一味屈从或归顺西方的阅读习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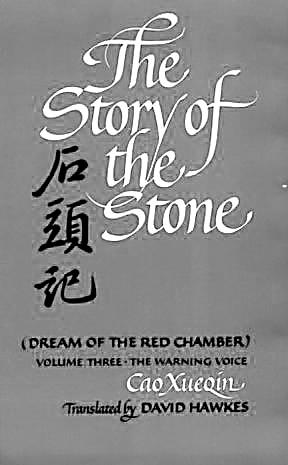
大卫·霍克斯翻译的《石头记》书影。本文图片均由作者辛红娟提供
在讲述中国故事、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时代当下,我们应当客观、公正地看待中国典籍翻译实践和接受之间的窘况与差距,从中国的典籍翻译大家身上汲取翻译的智慧,获取前行的力量和指导。在这方面,杨宪益先生,以及他与英国人霍克斯的两个《红楼梦》译本的比较,是一个值得我们静下心来认真反思的话题。
杨宪益,原名杨维武,祖籍安徽盱眙(今江苏省淮安市),著名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专家、诗人。1915年1月生于天津,1928年进入英国教会学校新学书院学习,1934年到英国牛津大学莫顿学院研究古希腊古罗马文学,认识了英国传教士的女儿戴乃迭,从此开始夫妻合作译书的世纪奇缘。杨宪益与戴乃迭合作,把《楚辞》《史记选》《青春之歌》《鲁迅选集》等百余种中国古今文学名著译成英文,总量逾千万字,在中外文学史上极为罕见,从先秦文学到现当代文学,跨度之大、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影响之深,被盛赞为“翻译了整个中国的人”。
20世纪70年代末,杨宪益与戴乃迭合译的《红楼梦》与霍克斯译的《石头记》几乎同时出版,三人皆因此获得巨大声誉,但也同时揭开了翻译界此后对两种译本经久不息的对比研究热潮。不足四十年的时间里,关于两种译文比较研究的论文和专著,可谓汗牛充栋,不仅有语词、称谓、服饰、意象、语篇转换等具体翻译技巧探讨,更有对译本背后传达的文化背景乃至意识形态的剖析。现有对杨宪益《红楼梦》翻译的研究文献中,四分之三以上都是将其与霍克斯译本对比进行的。众多的研究者、海量的研究文献、多维的研究视角,无论是质化的研究方法还是语料库的量化研究方法,占绝对多数的结论是:“杨译本”忠实原著,采用直译为主的方法,虽然对原文理解深刻,但语言略显苍白、文采不足,“霍译本”遵循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原则,以意译为主,英文流畅自然,饱满耐读,从传播和接受效果而言,“杨译本”远非“霍译本”可比,并进而得出中国典籍翻译还需外国人来做的简单结论。
杨、霍译本并非完全不可对照甚至对比,但我想强调的是,在研究开始之前,我们首先应当站在客观中立的观点,对杨、霍二人完全不同的翻译情境、翻译人生进行深入了解,更要从二者完全不同的翻译方向入手:“杨译本”系母语到外语的翻译行为,而“霍译本”却是从外语到母语的翻译行为,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翻译类型,不具有完全可对比性,分析得出的结论也因而不具有完全信度。作为中国译者,杨宪益具有高度的民族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以忠实为核心,偏重保留原文形式、结构和词序,尽量保留文字形象,体现出对原作者的尊重,对应原文程度较高,能够很好地起到传播中国文化的作用。当然,杨宪益译文也常出现因过于尊重原文,受缚于原文的文化荷载信息,而没能考虑到译文读者阅读接受的情况,但考虑到他为中国文学文化海外传播殚精竭虑的一生,皇皇译著,应算瑕不掩瑜。虽然杨宪益译《红楼梦》自问世以来褒赞与贬抑之声始终存在,但不得不承认,杨宪益与戴乃迭的合作翻译,秉承经典翻译与传播的良好翻译模式,为我们留下了丰厚的民族翻译资源。面对这份遗产,我们不应该绕道而行,甚而弃之不用,而是应该沿着杨先生的路接着走下去。同时在这过程中,我们应深入中国典籍外译事实,客观分析两类译本的优长与不足,汲取经验与教训,将中国的本土经验和理论与西方翻译理论相结合,取其精华,让中国的翻译研究与实践在传承和发展的良性循环中获得升华,在实践中不断培养和提高我们讲述中国故事、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时代能力。
中国的翻译事业必须具有充分的前瞻性和主动性,中国翻译界不仅要主动承担中国传统文化对外译介与传播的历史重任,同时也要大力加强对本土文学作品译出研究的力度,以改变外译汉及相关研究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局面,如此才谈得上增强文化自信,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
来源:光明日报 日期:2017年3月3日 文:辛红娟(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

